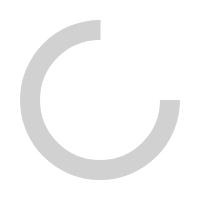香港出身國際級指揮家:一年飛300天的年輕廖國敏讓懶人無地自容
少年不識累滋味。
香港是國際級的金融城市,卻仍未是一流的文化藝術都會,那如何培養人才?說是簡單的:提供優秀的教育、包容的環境,把才華小鳥放離這置錐之地,看看世界,呼吸失敗、咀嚼欺凌,然後回來,立志為香港發光發熱。放下,再擁抱,「像極了愛情」! 近年,國際音樂界都知道,香港「出產」了一位三十來歲的世界指揮廖國敏(Lio Kuokman),因為肺炎疫情,他不能世界巡迴演出,關了在香港。Kuokman說:「也好。近年,一年飛三百天,睡醒了,張開眼睛,不知身在那一家異國酒店;現在享受『貼地』的生活,表面無所事事,但活出另一意義:斷了收入,穿回『街坊』裝,去尖沙咀誠品書店看看書、在朋友中環的咖啡室幫幫忙、學做barista、去西貢玩wakesurf。過去,天天在忙,現在尋回失去的時光。」對,工作和生活,好像栽樹和乘涼的因果。
和香港管弦樂團的要員Vennie Ho談天,她數十年來,看盡無數的名指揮家,Vennie說:「成為頂級指揮,要先天加上後天的努力,他們擁有四大能力:出色的音樂才華;第二,具清晰的溝通能力,帶領所有樂師發揮所長;第三,豐富的創作力,用自己的想像力去演繹作曲家的作品;最後,有超常的記憶力,最好把整個樂譜記下來,在演出的時候,便會一氣呵成;廖國敏是這類才華出眾的指揮家,他和樂團剛剛在7月初合作的音樂會,展現了他的功力。」我同意:「管弦音樂會要現場看,在好的指揮帶領下,看到近百枝弦弓,齊上、齊下,如石破天驚、風雷雨打,我的心會跳出來!」
Kuokman是香港和澳門的結晶品,有明燈才有影子:八十年代,在澳門出世,媽媽極愛古典音樂,四歲的時候,帶他去聽一個community orchestra,當看到台上有一個男人拿著一枝「筷子」在揮舞,便問媽媽他是誰?她答:「那叫做『指揮』!」自此,他立志要做那「筷子人」,於是請求媽媽送他去學音樂。五歲時,Kuokman開始學鋼琴,媽媽開玩笑:「如你沒興趣,便不要學下去,免得浪費金錢。」在十五歲那年,Kuokman贏了一個音樂比賽,獎品是香港演藝學院的一個週六音樂課程。每個週末,他孤零零地坐船來香港上課,然後又孤零零地坐船回澳門。如是者,Kuokman渡過了兩年的音樂人生。到了十七歲,演藝學院錄取了他,最初是兩年文憑課程,接著是三年的學位課程。2003年,Kuokman畢業,他說:「感受最深的是寂靜晚上的演藝學院,因為每天留在學校,一個人練琴到凌晨三時!」我開玩笑:「不怕鬼?」Kuokman失笑:「我唸書要靠獎學金,成績太重要,鬼也怕不了!」
我單刀直入:「國敏,怎樣才算是出色的指揮家?」Kuokman說:「利用指揮棒,由downbeat『颼』的一聲,他開始揮動精準而完美的樂韻,讓樂團隊友和觀眾同時水乳交融。」我問:「最困難之處是?」Kuokman笑笑:「是『一心三用』,即腦袋要處理三件事情:現在的moment,如何指揮好音樂?剛才的moment,有什麼不足的地方,一會兒如何改善?下一個moment,要如何處理,比這一刻更出色?」我好奇:「那你為何做得比其他指揮家好?」Kuokman謙虛地說:「也許是我的溝通及感受能力,因為在排練時我很快可以掌握及了解到某個管弦樂團的音質和各聲部的特點,也很快讓他們知道我想表達什麼,於是,八十五至九十五人的樂團,二十多種的樂器,便掌握於手中,當節拍一出,所有人和我一起出閘,編織一個震撼的音樂故事!」
我問Kuokman:「許多年輕人想跟隨你的成功之路,成為國際級藝術家,有什麼條件呢?」他搖頭:「我其實壯志未酬,不過,首要條件是鬥志,而且是『超級鬥志』。從演藝學院畢業後,我知道面前有一個個的事業『擂台』,而且我要爭取獎學金才可以打下去,如果我想做一個國際音樂家,便要闖世界級的擂台:第一個擂台便是打入成立於1905年,坐落於紐約市的頂級表演藝術學府The Juilliard School(茱莉亞學院),我唸的是鋼琴碩士,但是死心不息的是當指揮家。兩年後,從Juilliard畢業,我打算挑戰人生的第二個擂台:成立於1924年,『指揮』學科最有名的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柯蒂斯音樂學院),我興奮地告訴媽媽,決定以指揮為終身職業,她一貫地冷靜:『好,但你要考到全額獎學金,生活費,用自己的方法「搞掂」!』Curtis是極其嚴格的:它一年才收一至兩個頂尖的學生,老師對學生的比例是2:1,名師會天天督促你。可是,學院的三天考試是可怕地艱難:首先要過一個筆試,然後是聽覺測試,跟著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會擲來一份鋼琴樂譜,立即演奏;最後,要求我用短時間準備,指揮Curtis校內的管弦樂團,真的非常『攞命』。我慶幸打贏了這場仗,入到了Curtis,是我成功的半張入場券!」
我想起了香港電影《打擂台》的一句金句「唔打就唔會輸,要打就一定要贏,只要你敢打,你已經贏了自己」,廖國敏的鬥志,便證明了這點。
我聽了Kuokman的話,感動得很,再問:「此外呢?」Kuokman頓頓,吸了一口氣:「要有毅力,捱過生命的低潮。」我失笑:「你不是少年得志嗎?」他搖頭:「絕對不是!年輕朋友要記著,做藝術工作,一定要堅持信念,走過低谷,死不去,機會便會來臨。不過,『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在低潮時候,切勿轉行,或自暴自棄,應該利用這空檔,增強自己。當機會來臨時,人家考慮你是否『有料』的時候,立刻顯示實力,奪取這機會,如果到時才努力,一定來不及的!在2009年,我離開了Curtis,原本在費城郊區有一個小型管弦樂團給我第一份指揮工作,但是,金融海嘯突然殺到,它破了產,因此,在2009年至2014年的五年內,我過著浮浮沉沉的藝海生活,只好為學校做伴奏,在Boston住『板間房』,為了生計,到處找兼職,常常擔心生活。但是,我沒有放棄,凡有樂團請人,我會努力練習樂章,希望以最佳狀態去爭取工作,可惜往往事與願違。2014年,機會來臨了,我參加了法國一個著名指揮大賽,得了亞軍;跟著,五大樂團的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費城交響樂團,創立於1900年)聘請我做assistant conductor(助理指揮),這件事情從此改變我的命運。」
我們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人,「有錢沒錢」也應該天天做,已經不是熱情這般簡單,投入,變成一種信仰。小時候,我差不多每個星期寫一篇文章去報社投稿,還得省錢來買郵票。那年頭,沒有影印留底這回事,報社不用你的文章,連稿也不寄回,心血石沉大海,我常常對著空氣發呆,等待幸運。寫文章這件傻事,叫我傻到今天,但我知道世上會有人欣賞我;當年,父親把我徵文比賽冠軍獎狀,放入相架,掛在牆上。
我看著Kuokman趕吃他的意大利麵,問:「第三個條件?」他抬起頭:「是世界觀。做個世界級的藝術家,意味著你屬於地球,不屬於某處地方,舉例來說:我現在的家有澳門、香港、台灣、巴黎;演出地點包括歐洲、亞洲、美洲;我的經理人公司在英國,合作過的樂團包括莫斯科、上海、台北、波蘭,以及遠至西伯利亞的音樂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裏,星期日飛去一處新地方,然後適應不同的樂團、劇院、工作人員、食物、酒店,以至氣候,在週末演出後,匆匆的收拾東西,星期天又趕去機場,投入另一處演出的準備。我的行李箱是流動的家,放齊了春夏秋冬的formal或casual的衣服。我像一隻小鳥,飛呀飛,但是,這樣才能燃起我的鬥志,三百天在工作的時候,我精神奕奕,反而停下來休息時,卻病起來!」
我聽得毛骨悚然:「太可怕的生活,以我這個年紀,一定氣絕身亡。唉,擁有青春的,真討厭!現在流行online concert(網上音樂會),將來你會輕鬆一點吧?」Kuokman 語氣肯定:「現場聽音樂會,是全身細胞的立體享受,online是看著屏幕的活動,不可能相比,看情況,還是會有人找我飛去做guest conducting(客席指揮)的。而且,開玩笑來說,歐洲國家最願意花錢在足球和音樂這兩件事。在2017年,我離開費城交響樂團後,多了時間與世界各地樂團演出,讓我的音樂走遍世界,世界的音樂也流入我的血液裏!」
廖國敏的勤奮自立,應該讓許多香港年輕人汗顏。我們這些中年人,常常對著新一輩搖頭:疏懶、缺乏大志、諉過於人,大學畢業,還叫父母安排工作、支付婚宴、買房子。他們恐怕要刮骨療毒,才可醫治這種「脊椎彎」症。
在結束這次愉快的聚會之前,我問Kuokman有什麼話要送給香港的年輕人?他語重心長地說:「尋找人生,不要只往錢看,相信自己的興趣,把它變成信念,不要讓別人的享樂,成為你的引誘,要不斷磨鍊自己,但是不要『人比人』,應該和自己比較,今天比昨天進步嗎?明天又如何做得比今天好?好像很『老生常談』,但是,因為這些看法是真理,才能行之久遠。」 我同意:「有那些建議,送給香港和澳門的音樂發展?」Kuokman說:「能夠改善一下演出場地便好了,香港的音樂廳有點老舊,而澳門的,更只是一個綜合場館,日本、韓國、上海、深圳都在這方面比我們優勝。」
我笑道:「在外國多年,你有崇洋的心態?」Kuokman認真地:「絕對沒有。我在外國打拼,總會感受到種族歧視,哪會崇洋?只不過,古典音樂來自西方,我要尋根溯源地學習管弦樂,當然要往西方啦;假設我是一個川劇的演員,自然會飛往成都浸淫。」
「不入春園,怎知春色幾許」,我的大半生,徘徊於俗塵市集。有些年輕人今天變了,不俗氣,不是為錢而活,而是為夢想規劃未來,不要取笑他們,「看的這韶光賤」:有些朋友做了廚師、有些做了長跑教練、有些做了幼稚園老師,更有些去了難民營當義工。往後,大家欣賞一個人,不會因為臉上貼了多少塊金箔,而是在乎他的胸懷還滾動著多少動人的豪情!